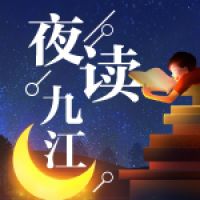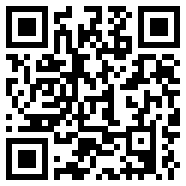悦读九江丨为故乡立传——《千帆过尽:鄱阳湖别传》代序
为故乡立传
——《千帆过尽:鄱阳湖别传》代序
□ 熊培云
2023年暑假,完成《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的首发,我自南昌返浔,上庐山,下鄱阳湖,会旧友新朋,在九江小住数日。其间与当地几位诗人和作家经常往来。有天晚上几个人准备在江边就餐,丁伯刚兄特别唤来一位老者,那是我多年来时常会想起的故人。
久别重逢,饭后我邀老人一起沿江散步。若不是因为天黑,按丁伯刚兄的意思,几人本可以跨过大桥走到长江对面的湖北黄梅去。据说他俩经常信马由缰,结伴而行,听得我好不羡慕。那种散漫、无拘又有友情缠绕的生活,随着我中学时代的结束已经难得一见。
借着这一次的重逢,此后的若干天里我和老人经常见面,听他讲述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及芳湖滩的男人和女人……而此前我对那些经历与见闻几乎一无所知。丁伯刚兄曾经特别谈到自己的这位伯乐,嘲笑他当年出门都带个梳子,是个过于精致的人。如今虽然上了一定年纪,老人给我的印象仍是目光炯炯。
老人说他每天早上都练半小时站桩,所以看上去并不显老。之后的某个清晨,我还在梦里,他趁着晨练的间隙给我送来一本《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的书。不得不说,打开信封的瞬间我被书名击中了。至于书里究竟写了什么,倒不是我急着要知道的。
翻开书,老人特别在扉页上为我题了几行字——“年轻时,什么都不信;年老了,信什么都不行。四十年前,我粉碎一切;四十年后,一切粉碎我。”
后面是他的署名——赵青。虽然此前只有一面之缘,这个名字我一直未忘。和他带过的编辑饶丽华女士一样,我喜欢连名带姓叫他赵青老师,这样显得更具体。赵青老师生在都昌,我生在永修,两家隔着鄱阳湖,都隶属九江。用他的话来说,鄱阳湖涨水时我们的村子就都属于鄱阳湖了。此话不假,记忆中1983年的那场大水,鄱阳湖里的大鱼是可能游到我家厨房的。
时光倒流三十年,认识赵青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我还只是云居山脚下的一名高中生,终日游游荡荡,时而逃学上山。由于热爱文学的缘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背着一部手写的诗稿和两个从食堂买来的馒头,独自去近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社投稿。大概是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学校创办了只有自己参加的一个人的文学社。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学会如何把“踽踽独行”之类的词语写进日记,我便开始胆大妄为地刻印蜡纸、油印社刊,并在全校各个班级赠阅我的诗歌与小说连载。
如果没有记错,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之所以对此念念不忘,实则因为那是我早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精神性事件,每分每秒不可谓不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羁旅北方,无论是重回还是路过九江,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的那次远行,包括在九江日报社遇到的那两位编辑——一位是青年画家兼美术编辑阳小毛,另一位就是最近与我久别重逢的赵青老师。
说回那个遥远的夏日,我们仨在编辑部聊了好一会儿,具体内容早已模糊不清,不过有个细节却一直记得。那是在临走的时候,赵青老师将我送到编辑部大门外,在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又转过脸对身旁的阳小毛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还沉重啊!”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年轻后生当年给赵青老师留下的印象首先是“沉重”二字呢?而在中学同学眼里我幽默、开朗,壮志凌云。可赵青老师是对的,因为他直接接触到的是我的文字,里面不仅潜藏着我与生俱来的某种气质,同样沾染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特有的忧郁。在那个年代,虽然人心向上,翅膀却仍然是沉重的。
有些沉重来自现实。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但对于农家子弟来说,有些阳光是用来告别的。就像张雨生在《我的未来不是梦》里唱到的“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须知夏日之酷暑难当正是无数农人及其后代逃离乡村的理由。赵青老师曾经提到他十五岁那年带着个篾箱第一次来九江城,从独轮车到渡船,一百公里的路足足花了三天三夜。
这一切,几十年后我在赵青老师身上也看到了。他的口头禅是能像沈从文一样,以此一生造一间希腊小庙,在里面供奉人性。而他的幸运在于年轻时没有彻底走上仕途,而是借着一次次落难,如王一民先生说的一样,热爱文学的他“像一片落叶一样飘到了湖口”。
我们常说时光如矢,一去不返,可生活有时又像是一个个轮回。几十年前,赵青老师在一个乡村少年身上看到某种沉重的东西。几十年后,那个长大的少年同样在前者身上看到了久违的沉重。这种遥远的呼应解释了为什么几十年间我一直对当年的那次远行与相遇念念不忘。如今当赵青老师感叹“生活在恶的时代人们会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名副其实”时,我也仿佛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年纪与境遇,赵青老师当时无意间对我特别提及的“沉重”,本质上说也是无数追求精神生活的人长有的生命之底色与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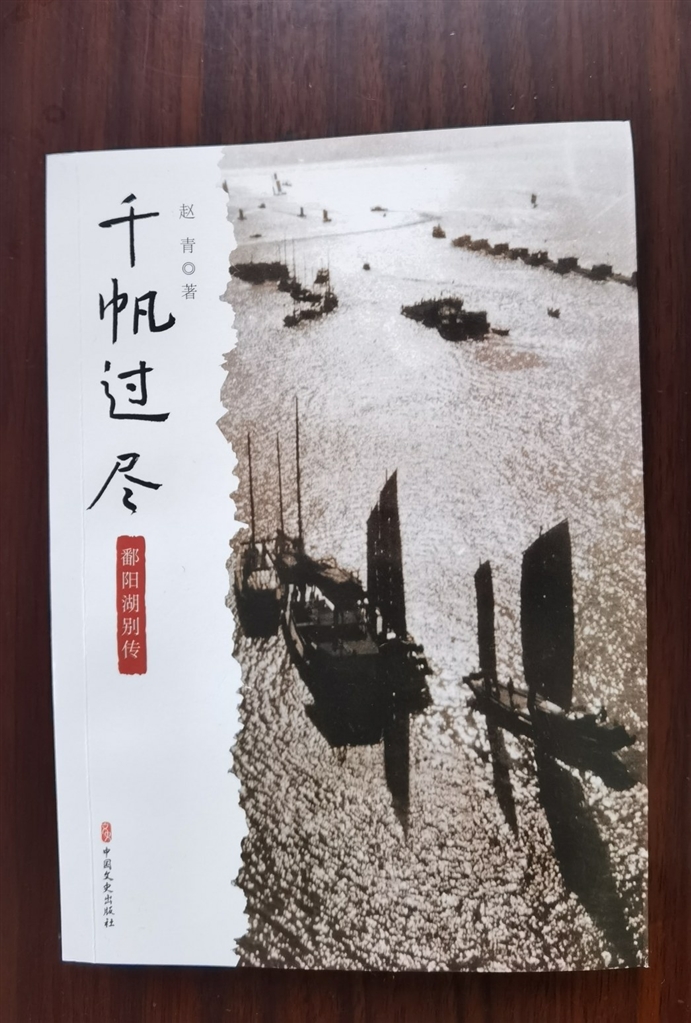
接下来言归正传。当赵青老师邀我为《千帆过尽:鄱阳湖别传》写序,我自知这实非我之所长,任何简单赞美或批评对我都是艰难的。在九江的日子,从茶馆、寺庙到风景,许多事物着实让我印象深刻,而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我的呵护以及对本乡本土的热爱。赵青老师这些年来的写作多与这片土地有关,而这次有关鄱阳湖及其周边风土人情与地理、历史的梳理,虽然书中更在意的是资料性而非文学性,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其在“为故乡立传”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在书中作者特别谈到一种在野的状态,而鄱阳湖及其周边无疑有着不负盛名的江湖之远。在写到洪范时,有段话读来感人至深:“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叶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永久沉默的空间。”
还记得那天我和赵青老师坐在长江边上聊天,对岸的黄梅正下着暴雨,九江这边也顺势刮起了狂风,而我们并排坐在风里都不忍离去。当时我在想,在这片被称为“吴头楚尾”的地方,如果我不曾远走他乡,而是一直在本地生活,我会以哪种方式记录脚下的土地与河流。回想此前在庐山遇到的一些朋友,我们不仅一起拜谒陈寅恪先生夫妇的墓园,还同在山间尽情感受在夏天吹着春天的风。之后又去了鄱阳湖畔一边赏月一边听附近渔民回忆湖边往事。此外也和不同的朋友访问了一些住持与僧人。唯一遗憾的是,在与庐山图书馆李朝勇兄同游东林寺时再也没找到藏经楼外的对联——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印象中那副对联是十几年前我回九江做讲座路过时偶然见到的。因为比较符合自己的心境,从此一直念念不忘,不知何故今已不知所踪。
感恩于年少时的一段机缘以及后来的重逢,所以有了以上这些文字,起身回顾时始觉不知所云。今日世界变动不居,无数人都在同时感叹“故乡之沦陷”与“彼岸之沉沦”,所幸同样有无数人在借助文字和思想的力量默默守卫乡土与世界。而我们最终走向何方,的确需要用一生的光阴来回答。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这颗孤独的蓝星上,相信我们终此一生的所有努力也都是在为自己精神之故乡立传吧。至于将来如何,就像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所感叹的,人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抱怨,除了变得更好。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钟千惠
责编:许钦
审核:姜月平